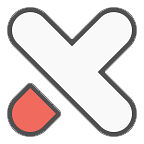多份施工合同均无效的,工程价款参照实际履行合同约定的价款折价补偿
- 工程价款
- 2024-08-21
- 159热度
- 0评论
【方法解析】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一)》第二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就同一建设工程订立的数份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均无效,但建设工程质量合格,一方当事人请求参照实际履行的合同关于工程价款的约定折价补偿承包人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在实践中,如果当事人对实际履行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产生争议,需要根据施工过程中发包人、承包人以及监理等的往来签证、会议纪要、通知、函件、工程款收支凭证等证据,对比几份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约定不同之处,综合判断当事人究竟履行的是哪份施工合同。因此,多份施工合同均无效,工程质量合格的,工程价款参照实际履行合同约定的价款折价补偿。
【解析规则】
多份施工合同均无效的,工程价款参照实际履行合同约定的价款折价补偿
(2017)苏民终2207号
案情简介:
2010年8月16日,某建公司与万某公司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一份,约定万某公司将其开发的某住宅小区7号楼扩建及5号楼、6号楼、7号楼B区未完成工程的土建、安装工程发包给某建公司,资金来源是自筹。2010年8月18日,双方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补充协议》一份,约定的工程概况、承包范围与2010年8月16日合同一致。同日,双方又签订一份《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补充协议》一份,约定:超市主体完工时间为113天,合同签订时乙方向甲方交工程保证金400万元元。上述两份补充协议均注明“2010年6月19日所签补充协议作废"。2013年5月8日,双方再次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一份,第五条“合同价款"约定为6450万元,同时注明“以审计为准"。在前述合同签订之前即2010年6月22日,某建公司与徐某某、案外人顾某某签订《承包工程内部协议书》,约定由徐某某、顾某某承包某小区5号楼、6号楼、7号楼扩建工程,工程造价6500万元,建筑面积62854平方米,框架结构。徐某某、顾某某按工程总价(决算价)的2%上缴给某建公司。工程质量等级为合格。工期360天,自2010年6月22日至2011年6月30日。付款方式为“按大合同"。后顾某某退出合伙,涉案工程由徐某某出资并实际进行施工。2014年2月27日,万某公司(甲方)与某建公司(乙方)签订协议书一份。上述协议达成后,双方均按约履行。万某公司共支付徐某某工程款456万元。2015年4月23日,万某公司(甲方)、某建公司(乙方)及徐某某(丙方)签订《天成小区5、6、7号楼交接协议》一份。
某建公司认为万某公司没有向其支付全部工程款,双方协商不成,因而成讼。
一审法院认为:
关于涉案工程价款如何确定的问题。根据查明的事实,针对涉案的工程,万某公司与某建公司签订了四份合同,即:2010年8月16日合同、2010年8月18日补充协议1、同日签订的约定造价为8395万元且约定“具体金额以决算报告为准"的补充协议2、2013年5月8日签订的约定造价为6450万元且约定工程造价“以审计为准"合同。上述四份合同中,2013年5月8日合同系为补办涉案工程建设许可证及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手续而补签的招投标备案合同,违反了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且签订该合同时,涉案工程早已开工建设,故该份合同显然不是双方实际履行的合同,不具有法律效力,故不应以该合同的约定作为认定涉案工程造价的依据。其他三份合同,均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且无法律规定的无效情形,均应认定为有效合同。其中2010年8月16日合同签订时间早于2010年8月18日的两份补充协议,2010年8月18日的两份补充协议则对2010年8月16日合同中的相关权利义务进一步进行了约定,故上述三份合同均应认定为双方实际履行的合同。因该三份合同对工程造价的约定并不一致,且在工程实际施工过程中,工程量发生了变更,双方对此未作出其他约定。此时,如以2010年8月18日约定固定价6450万元的补充协议确定涉案工程的价款,与实际情况不符,且有失公平。故某建公司主张双方对工程造价约定不明,应当进行审计的意见应当得到采信。本案应当以天园公司的鉴定报告作为认定涉案工程造价的依据。根据前文所述,涉案工程造价中,某建公司应得款项应当为:无争议部分86857187.7元+有争议部分中的第1-4项2293774.08元+第7-8项1602755.63元(未扣减万某公司代付的50000元及应支付赵南山的300000元)=90753717.41元。
2014年2月27日协议中约定“甲方(万某公司)在6450万元工程款外,再支付500万元工程款给乙方(某建公司)",此仅是某建公司与万某公司对后续工程款付款节点的约定,并非对涉案工程总造价的确认。如前文所述,6450万元的工程造价与天园公司审计的造价相差甚远,明显对某建公司不公平,故不能以此作为认定涉案工程总造价的依据。
万某公司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
二审法院认为: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一条规定:“当事人就同一建设工程订立的数份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均无效,但建设工程质量合格,一方当事人请求参照实际履行的合同结算建设工程价款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实际履行的合同难以确定,当事人请求参照最后签订的合同结算建设工程价款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中,虽然就同一工程订立的数份合同均无效,但涉案工程已交付使用,应视为建设工程质量合格,故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双方可以参照实际履行的合同结算工程价款。关于实际履行的合同,从本案数份合同所载明的工程价款结算依据看,2018年8月16日合同和2018年8月18日补充协议1均约定为固定价6450万元,而2018年8月18日补充协议2约定为暂定价8395万元(具体金额以决算报告为准),2013年5月8日备案合同约定为暂固定价(以审计为准)。庭审中,某建公司、徐某某主张上述合同存在混合履行的情形;万某公司则主张实际履行的就是2010年8月16日合同和2010年8月18日补充协议1,而非2018年8月18日补充协议2和2013年5月8日备案合同。对此,本院认为,2014年2月27日协议系双方就涉案工程签订的最后一份协议,从该协议载明的内容看,签订该协议前工程已停工,双方经协商后约定由某建公司全部完成剩余工程,万某公司在6450万元工程款外,再支付500万元工程款;万某公司支付50万元启动资金后恢复正常施工,然后再按施工节点支付剩余450万元。由此可见,双方在涉案工程即将完工时仍确认工程价款为6450万元,万某公司同意增加500万元系为了顺利完成收尾工程,并非系为了支付工程进度款。因此,根据2014年2月27日协议载明的内容,足以证明双方实际履行的是2018年8月16日合同和2018年8月18日补充协议1。一审法院仅以双方在该协议中就增加的500万元工程款分施工节点支付,即认定该协议为工程进度款协议不当,违反了该协议第一条双方明确约定的订约目的,对此本院予以纠正。双方实际履行的合同为固定价格合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二条关于“当事人约定按照固定价结算工程价款,一方当事人请求对建设工程造价进行鉴定的,不予支持"的规定可知,一审法院以天园公司鉴定的工程造价作为双方结算工程款的依据,不符合法律规定,本院对天园公司出具的工程造价鉴定意见不予采信。本案工程价款应以固定价6450万元加上万某公司同意增加的500万元即6950万元为依据。
某建公司、徐某某不服二审判决,申请再审。
再审法院认为:
根据二审判决核查认定的事实,徐某某系挂靠某建公司的实际施工人,某建公司、徐某某在申请再审中对此并未否认,且徐某某也自认其作为实际施工人有权向发包人主张权利。由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关于“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的规定,认定无效:……(二)没有资质的实际施工人借用有资质的建筑施工企业名义的;……"的规定,二审判决认定某建公司与万某公司签订的2010年8月16日合同、2010年8月18日补充协议1、2010年8月18日补充协议2、2013年5月8日合同、2014年2月27日协议,均因违法无效,有相应的事实和法律依据。
关于实际履行的合同,应结合合同签订时间、合同内容、是否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等因素综合判断。当事人就同一或者相关事项签订多份合同且没有特别说明的情况下,各方权利义务的确定原则上应遵循以后签合同为准的原则,后签合同未涉及或者未约定的仍遵守在先合同的约定,但有证据证明后签订合同并非实际履行的合同除外。从时间顺序上看,2014年2月27日协议系双方就案涉工程签订的最后一份协议,从该协议载明的内容看,系双方为使工程迅速完工,就某建公司恢复正常施工、完成剩余工程,万某公司在原工程款外再付500万元工程款事宜达成的协议,其中该协议第一条明确载明:“双方一致同意,乙方(某建公司)全部完成上述工程,甲方(万某公司)在6450万元工程款外,再支付500万元工程款给乙方,其中200万元用于为徐某某支付法院(2012)宿中商初字第0144号判决书的执行款,300万元用于未完工工程建设";第二条规定了该500万元工程款分期支付的具体节点。由此可见,双方在案涉工程即将完工时仍确认工程价款为6450万元,万某公司同意增加500万元工程款系为了顺利完成收尾工程,而非为了支付原约定的工程进度款。就此考察在该协议之前签订的其他四份合同中,除2010年8月18日补充协议2外,2010年8月16日合同、2010年8月18日补充协议1和2013年5月8日合同均约定案涉工程价款为6450万元。该三份合同中,2013年5月8日合同在明确约定工程价款为6450万元的情况下,又加注“以审计为准",并在专用条款第23.2条“本合同价款采用"栏中填写为“暂《固定价格合同》以审计为准"。从形式上看,2013年5月8日合同在表述上与在先签订的2010年8月16日合同、2010年8月18日补充协议1的约定不完全相同(2010年8月16日合同、2010年8月18日补充协议1中没有“以审计为准"“暂"的表述),但是基于二审判决核查的事实,诉争双方当事人对于“以审计为准"“暂"手写部分是否系某建公司时任法定代表人王道荣事后添加的内容存在争议,难以认定该表述系双方一致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从2013年5月17日招投标备案表以及2013年6月22日补办的施工许可证载明的内容看,双方在签订2013年5月8日合同并备案后办理行政审批手续过程中,仍明确合同价格6450万元,并无“以审计为准"的表述;而截至2013年5月,徐某某已完成大部分工程施工义务,此时再签订所谓备案合同的目的,双方表述差异较大。某建公司、徐某某主张是因在施工过程中工程发生了变化,双方根据工程的实际变化情况对2010年8月16日合同中的工期以及合同价款进行了变更;而万某公司则认为是为应对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的检查而完善招投标程序和补办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关于2010年8月18日补充协议2,与前述协议约定不同,明确工程价款为8395万元,具体金额以决算报告为准。显然,该补充协议与2010年8月18日补充协议1及其他三份合同约定的工程价款为6450万元差异明显。万某公司主张双方签订该补充协议系专门用于向税务机关报送案涉工程成本,并非为了案涉工程施工。对万某公司上述主张,某建公司虽不予认可,但没有提交相反证据予以反驳,某建公司亦认可该补充协议在其签字后即被万某公司取走,其不持有该协议的原件,甚至连复印件亦没有保留的事实。而且双方在同一天明确约定工程价款为固定价6450万元的情况下,又签订补充协议约定工程价款8395万元且以决算报告为准,不合常理。二审判决基于前述事实,结合在后签订的2014年2月27日协议约定以及案涉工程施工进度、工程量变动、工程手续补办等相关案情,认定万某公司的陈述更具可信性,双方实际履行的是2010年8月16日合同和2010年8月18日补充协议1,而非2010年8月18日补充协议2及2013年5月8日合同,有相应的事实依据,并无明显不当。